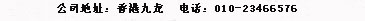中医伤科不仅仅是ldquo理筋正骨
——薛己·《正体类要》
屈指早年十分喜欢以“中医骨伤科医师”自居,缘由除了给病人可以扳得“咔咔”响之外,也有要区别于“推拿按摩”的意思。中医行业有许多行骗的噱头,比如“佛医”、“道医”或“XX单传秘传”之类,近年来还兴起有所谓“古中医”的叫法。无非是为了“区别自己与众不同”而已,因为中医的许多治疗方法和技术都给人很平易近人的感觉,比如悬灸法再说得天花乱坠也无非是拿根艾条灸而已,于是不得不用“XX神针”、“XX神灸”、“X为灸”之类的标签体现自己的与众不同。
这种情况到了“手法治疗”这个行业,就变得更加变本加厉——反正无外乎“揉揉、按按、摸摸、扭扭、拉拉”,谁搞都是这一套,怎么体现自己的与众不同?只好巧立名目起来了。
不少朋友都知道,屈指本人其实是一个爱好曲艺的文艺青年
“手法治疗”偏偏还是一个完全没有准入制度的行业,从处于江湖之远的街头洗头房到居医院,都有不同水平的“手法疗愈”从业人员——之所以称为“疗愈”,是因为对于没有医师证的人而言,他的各种宣传中绝对不能出现“治疗”的字样。
我并不否认许多“民间高手”比专业人员的水平更高,但那需要长期刻苦的专门训练,作为回报的是:这些人往往并不愁病人,生活水平也教平均水平为高。这些人完全不必借助新媒体就可以维持自己体面的生活,许多时候甚至衣食无忧还可以泽被一两代子孙后代的生活,水平差到我这种程度,才需要没事刷刷自媒体体现一下存在感。
本文的要点是:
1、中医骨伤科作为中医学的一个分支,具有中医学的属性,治疗方法除了“理筋正骨”之外,内外用药也是很重要的部分;
2、中医骨伤科有一门特殊的学问“内伤病学”,来源于先人长期的临床实践,这门学科认为许多病症来源于“形体损伤”,药物治疗的方法与中医内科用药之“气血阴阳”的辨证方法不同;
3、从某种意义而言,“点穴”是一种典型“形伤”,可以按照“内伤病”的方法治疗;日常可能遇到形伤的状况。
回到本文开头的那句话,早年我经常用于讲课。无非是跟人强调认识“形伤”的重要性,并且经常:“您看这种形体损伤,不是单用中药能够治疗的,还必须要手法治疗”云云……
直到某一天从头到尾看了一遍《正体类要》这本书——其实这书仅仅是薄薄的一小册,突然发现薛己其实并不太重视手法治疗,按照所谓《中医骨伤各家学说》的分类,他属于强调“用药”的流派;与之对应的,是《医宗金鉴》以“七分手法、三分药功”为主要观念的“手法治疗”派。
在后来的学习当中,我本人也恰好见过这两种治疗理念的一些老师,他们各自的对本体系治疗技术的坚守简直达到让人惊为天人的境界。金庸先生的《笑傲江湖》当中,描述过华山派的“剑气”之争,在中医骨伤科当中也不乏这种争论,比如“理筋”与“正骨”、“用药派”与“用手派”之争。在万恶的旧社会,通常情况下徒弟都会拿着师父的指示当圣旨,存在这种争论的结果往往是将各自的技术发展至极限。
针灸理论当中有一种思路是“以药性概括穴性”,认为“穴位”具有类似药物的药性,通过分析穴性来配伍腧穴以期达到治疗疾病的目的。这种“分析”在实践过程当中往往“呵呵”,因为缜密分析过之后,你会发现其实扎的还是那几个穴位。对于用药VS用手这种事情上,许多人的疑问是:“手法是一种物理作用,怎么用药物的化学作用替代呢?”
比如“骨折”这种病,如果不能纠正骨折移位即便是“愈合”也是畸形愈合会影响肢体的正常功能。屈指早年曾见过京东一位民间中医治疗患者“O”形腿的过程:
医院的管理尚不似近年来之严格,这位民间中医——姑且称其为Z先生,先让病人找了一个“关系”办了住院,然后开始给病患服用一种中药粉剂。一段时间之后,又用一种自制的药液给病人的腿股部(包涵膝踝关节)进行泡洗熏蒸,时间持续数小时之久,然后让病人家属移动病人至病床之上用布带固定患者双腿就像包裹婴儿双腿一样。反复数次之后,发现这个病人的“O”型腿确实有所改善。这个病人的诉求是想解决自己的“风湿”,至于当初的诊断是“类风湿”还是“骨关节炎”,当年因为我个人年幼无知也无从可考了……
这个故事乍听起来颇为玄幻,仔细思考确实有一定道理,之前我们无数次强调人体是一个“粘弹性体”就是在持续外力的作用下会发生形变,所以会有“腰椎间盘突出”或者“骨质增生”这些疾病。骨骼本身也并非不能变形而是有一定的可塑性的,比如骨折之后就会重新塑造形态,整容手术当中许多增高术的原理也来源于此。那么如果用中药创造一个适合骨骼及肌肉、筋膜等结缔组织重新塑形的机体“内环境”,一些简单的“矫形”是可以完成的。
中医伤科用药往往注重局部给药——比如膏药、罗汉神针(一种特制的艾条)或者泡洗熏蒸之类,局部给药无疑可以提高药物在局部的浓度,也可以通过调整局部气血抟散的状态影响筋骨的状态。
普通人(甚至包含许多中医内科大夫)认为手法是操作性的技术,熟练程度不同水平自然不同,方药这种东西方子都是纸上记着的只要辨证准确谁开都是一样的——于是有“中医无秘方”的说法;其实不然,当年山东有一位伤科名家梁铁民手头有一个膏药专门治疗骨结核、骨肿瘤,后来却失传了。屈指找当地比较了解内情的朋友问了问,说:“方子还在后人手里,膏药熬不出来了呐!”对于中医而言,“制药”也是一门十分复杂的技术,单靠看书没有实践和老师指导往往也不能成功,所谓“自古传丹不传火,从来火候少人知”的说法其实是说外丹术的。手法治疗同样如此,比如一指禅推法书上写得清清楚楚,练习时仍然一头雾水,或者用着用着手开始疼,没有老师指导自己往往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
手法治疗的长处则是可以定点定位定层次,我个人就认为对于许多局限性疾病比如“鼻炎”、“中耳炎”、“麦粒肿”或者其他的耳鼻喉科疾病、疮疡之类,手法治疗就比中药治疗见效快。因为可以解决局部气血循环障碍的问题,这些疾病单用药物往往出现“局部血药浓度不足”的窘况——即药物没有到达需要治疗的局部。
“点穴术”就是一种定点的治疗方法,对于从事手法治疗的同行而言并不陌生,这种技术的另一个用途却是“伤人”。从技击角度而言,我本人并没有“被点穴”,但却见过一些会点穴的朋友,也向他们请教过一些点穴术的原理,发现这门技术并不太好学,比如我的朋友只能做到双方静立不动时“点穴”,使人肢体麻木、晕倒或者肢体疼痛之类。至于真正能够在技击当中实践,据说需要许多针对性的训练。这些点穴制人的效果,大多可以从解剖来解释,以色列有一种马伽术攻击也多集中于这些“穴位”。
因为所谓“传说”往往越传越具有神秘色彩,以致于经常被“走近科学”……
点穴术之“限时取命”的传说十分神奇,据说可以“杀人于形”,即被“点穴”之人当时并不发作,待过后若干时间才会发作。这种设计颇为符合中国的国情,比如万恶的旧社会泼皮牛二抢青面兽杨志的宝刀,杨志如果会这种“限时取命”的技术,只要点中牛二的穴道再悄悄尾随等着牛二“穴伤发作”再把宝刀拿回来即可。又或者赶上拆迁一类的群体性事件,点穴专家大可以一展身手……
近代略为有据可考的“点穴制人”的事迹,见于郑怀贤教授和沪上名医金针黄石屏,之所以称为“有据可考”也仅仅是多人转述或记于某人笔记而已,我本人也希望有缘能够见到传说中的“沾衣摸穴”、“限时取命”的世外高人。
在中医伤科手法当中,“点穴术”是重要的治疗技术——其中比较特殊的方法是任督流注点穴术,这种方法记录于《救伤秘旨》等多种伤科古籍或者抄本上:
血头行走穴道歌
周身之血有一头
日夜行走不停留
遇时遇穴若损伤
一切不治命要休
子时走在心窝穴
丑时需向涌泉求 对口是寅山根卯
辰封天平巳风头
午时却与中脘会
左右命宫分在未 凤尾属申封门酉
丹肾俱为戌时位 六宫直等亥时来
不教汝搏斯为贵
不同的抄本略有不同,这些穴位的名称并不见于《针灸学》实际的位置却很相似——大多位于任脉与督脉之上,原书中也有这些穴位损伤的治疗方法,大多是主治方剂加手法治疗的模式。许多人诟病“现代中医”不治病,现行的医疗行业状况是医师越来越像流水线上的一个环节,并不能使出“浑身解数”来应对具体的病人。不仅仅是中医,西医也是如此,当病变比较局限时反而更容易得到明确有效的治疗——比如外科手术切除,做完手术一律都可以“治愈”;但当局限病症是整体失衡的结果而非原因时,治疗就总是差强人意……
这种任督流注点穴法不仅仅用于制人也可以用于“治人”,许多定时发作的疾病可以选择这种思路来在穴位上施治,这就不仅仅是纠正结构的“理筋正骨”了,还包涵对人体气血的调整;就如同华山派的“剑气之争”一样:原本用于调整“气血”的内外用药,在中医伤科看来却可以“治形”;而原本应该用于“调整结构”的手法治疗,反而可以用来“调气”。
“点穴”对于人体的损伤也是一种典型的“形伤”,用极大的力量点击身体的某个解剖弱点会损伤皮肉筋脉骨的“形体(相关阅读中医形体观)”部分,用一般中医内科“气血阴阳”的思路开方自然无效;需要用前述中医伤科的思路才可以。日常生活当中其实可能遇到“被点穴”的情况,就是当受到外力撞击时,外力沿着骨架的方向扩散有可能对身体造成深远的影响——比较常见的情况是崴脚之后魔怔般总崴脚,现代医学自然有本体感觉或者关节运动学方面的解释,中医伤科除了用“筋出槽、骨错缝”来辨识之外,丘墟穴(鞋带穴)的穴伤也不容忽视。长时间的足踝损伤也会对全身产生影响,最常见的症状就是内科辨证属于胆气不降引发的耳鸣、头晕等症状,反之当遇到这种情况的病人时如果胆经的丘墟脉口有异常的变动,则可以在这里进行治疗。
许多朋友觉得有时候看了这个
转载请注明:http://www.fifundesign.com/etzey/6539.html
- 没有推荐文章
- 没有热点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