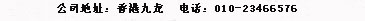连载十六金丝楠木安戈换肝记
七十二
热,太热了。要问我手术后什么感觉,就这一个字。
护士姑娘又给我弄来三坨冰,一坨放脚边,两坨放脖子边。三个冰坨子包围着我,总算把热气压了下去。
这一天,陈知水教授和蒋继贫医生不断地轮流进来看我,一会儿来看一次,一会儿来看一次。我不知道一个刚醒过来的手术病人,让他的医生怎样的牵肠挂肚。
下午,随着麻药的苏醒,我渐渐地就兴奋不起来了。伤口一开始是慢慢的疼,后来就狠狠的疼。不过,这种疼痛也就是单纯的疼痛,是一种新生的疼痛,可以忍受的疼痛,是有希望的疼痛。所以,疼痛中蕴含着一种快乐。
再就是虚弱中的燥热,不想说话,不想动,不想糖吃了。由于手术后使用了大量的溶血药物,口腔也起泡。这种泡不能戳破它,只能任由它自生自灭,一旦破裂,流血难止不说,感染的风险也就加大。
原来,上午的兴奋状况和良好感觉,只是手术中大量使用激素所造成的暂时现象,激素能抑制排异,也能缓解症状,还能制造热。我自己还不知道,我还远远没有脱离苦海,我还站在奈何桥上,一边是死神,一边是陈知水,他们像在拔河那样拉着我。我正处于高度危险期,我还是重症病人,危险随影而行,任何一种风险都是要命的。这个时候的陈知水也应该是最紧张的时候。一个病人外科上的问题,同时也是内科上的问题。蒋继贫医生说过,一个好的外科医生,同时应该是个好的内科医生。为什么有的人手术做的很成功,最后却没能把人救活,一般问题都出在内科上。
第二天,发起烧来,随之右边耳朵下面开始肿胀,很快就鼓起一个大包。医学上叫中耳炎。
中耳炎是病毒性感染,传染性很强,特别是在重症监护室,如果传染开来,可就是麻烦大大,我也是雪上加霜。不知道陈知水紧张不紧张,反正我是真的一点都不紧张。这东西我熟悉,小时候得过,当地叫抱耳风。用桐油放在铁片上烧,烧的滚烫在冒青烟了,再往包包上那么一“兹拉”,几天就好,等抱耳风好了,再去治疗烫伤。
所有的这一些,对于我来说,都是一个生命开始所必须经历的,是成长中的代价,和手术前的痛苦具有本质区别。这一点我很清楚,因此,我的心态也不一样,只觉得是快乐中的痛苦,无所谓的啦。
我估计,陈知水和他的手术团队可能是没怎么睡觉,就是睡觉了,也是不安稳的,因为中耳炎那个东西传染性很强,这么小的重症监护室,空气流通不畅,病人又多,不好控制。
为了切断传染源,不使我传染给其他病人,陈知水教授决定把我隔离起来。
护士长为我单独腾出一间病房,整了一间无菌室。我在重症监护室住了两天后,出了ICU,住进隔离室。
医院病房
七十三
这是一间由普通病房改成的重症监护室。
病床置于房间的中央,四周都是可以活动的空间。窗明几亮,房间整洁,空气清新。门口,除了门,还有一个白色的帘子。进来的人要先在帘子外面更衣、换鞋、带口罩,全副武装才能进来。
一个护士进来,绿色的防护服,大口罩,大防护帽子,在我的周围转来转去。一会儿用棉签沾上水塞进我的嘴里,一会儿用一块纱布擦拭我的汗水,很是贴心。这个动作我很熟悉,我妻子就是这样给我喂水喝的,一个护士也能做到如此细心,让我感到很温馨。
我睁开眼,是我妻子。
我笑了。
这谁想出来的主意,想得真周到,让一个病人家属去做如此精细的护理,不了解内情是不会这么做的,感叹陈知水和他的团队良苦用心,真的是贴心啊。
我不解妻子的全副武装,说,我有那么可怕吗,我有那么严重吗,值得如此如临大敌?
她说,“不是怕你的什么传染给别人,是怕别人的传染给你。”她告诉我一个道理,移植手术中使用了大量的抗排异药物,病人的免预力是零,对微生物没有一点抵抗能力,很容易造成感染,因此要保持隔离,避免接触。
这么一说我就懂了。不管是医生还是护士,进病房时都从头到脚包裹的严严实实,为的是病人不受到外来微生物感染,并不是害怕病人感染他们。
术后第一个星期是高危期,除了器官的急性排异,最大的风险来自感染,中耳炎就是感染所致。
术后第五天,护士给我做完雾化,我真切感到她把雾化器上面的细菌通过雾化器的吸入口,直接贯通到我的血管里去了,感染了我的血液,我的血管立马产生了异样反应,引起呼吸道不舒服。我把这个重要情况告诉我妻子,要她喊医生作出紧急处理。可我妻子却只喊来护士,让她用棉签给我消毒。
消毒还是不管用,我的想法是,要将一种消毒药灌进血管里,或者将血液通过一个过滤机那样的设备过滤,这样才能杀死细菌,保证安全。可是护士不听我的申述,只是在我强烈要求下,才又用棉签擦拭我的口腔。过了一会儿又不舒服,只得又叫护士,如此反复,护士也不厌其烦。一会儿又觉得房间里太闷了,想要出去转转,呼吸新鲜空气。为此,我一遍一遍的催促妻子,可是,这个平时对我很好的她,竟然只把个病床在病房里挪来挪去来忽悠我。难道没出病房我也不知道吗。一天一夜就这样来来回回。我才不听她解释,我觉得应该叫蒋继贫来,兴许他能帮到我。妻子熬不过我,去找蒋继贫,回来说蒋医生不在,护士行吗?我说不行,要不找陈知水。
陈知水来了,也只安抚了几句,说雾化没问题,血管也没问题。说我这些反应都是正常的药物反应。听他跟我妻子说,我这还是轻的,有一个病人是报社主编,还穿越了,在走廊里叫嚷、喊口号。要把那个谁谁谁揪出来,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他穿越到文化大革命时代去了。由于大量剂量的抗排异药物的使用,生理上无法适应,会产生药物性神经错乱,表现为兴奋异常,出现幻觉。
这样的情况持续了两三天。虽然折腾,磨难多多,倒也总体平安,渐渐地,抱耳风得到控制,口腔里的血泡也小多了,只是对怀疑的感染问题一直耿耿于怀,但程度没原来严重了。
重症监护室,这是网上找的照片,医院移植病房好像没这么大
七十四
一个星期后,我顺利地度过危险期,进入平稳恢复期。
小孟来给我换药。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自己的伤口。比想象中的还要大,还要难看。一条从胸口出发,朝右边方向,沿着肋骨边行走,直达腰间。一条从同一起点出发,往左直达肋骨尖。整个一个大写的人字,人字下面还并排打了等距离的三个孔,比铅笔还粗的橡胶管从里面引出液体,通过半透明的引流管,汇集在袋子里。有红色的,是血水,也有咖啡色的,是胆汁。还有混合色的,是体液。这些东西一天能把袋子装得满满的。
自从9月13号倒下,已经在病床上躺了一个多月了,看到的世界全是横着的。长时间卧床,使皮肤对床反应强烈,一挨上去就火辣辣的疼。又不能翻身,动一动都会扯动伤口,只能那样平躺着。伤口的疼加上背部皮肤的疼,联合攻击,是很难受的。
典型的一天是这样度过的:
早上天刚亮,疼痛了一夜的我还在梦中,护士进来,打开床头灯,或量血压,体温,或抽血化验,新的一天就开始了。妻子先将一块无纺布铺在我身子下面,打来一盆热水放在病床前面,将毛巾浸湿,抹上香皂,先把脸上擦一遍,然后将毛巾洗干净,换一盆热水清洗一遍。再换一盆水按照身子、重要部位、脚的顺序依次擦拭一遍。这一遍下来要换六次水,打三次香皂,搓17次毛巾。接下来是刷牙,牙我自己刷,她只把毛巾接在我的枕头边,刷完后头一偏,吐到毛巾上。涑口也是这样做,她只管洗毛巾就是了。这一遍下来,浑身清松,精神爽朗,感到虽是住院,可日子还是蛮悠闲的。
看到日头升起,想起小时候我跟父亲到溇水河放鹭鸶,到了一个深潭,月亮还没有落山,我父亲便在岸上烧一堆火,一边烤火,一边跟我讲大山外面的事。说,顺着这条河下去,有一个叫津市的地方,那里的房子有好几层,每一层都住人。每一层都有一个靠河边的窗子,人就坐在窗户边喝酒。喝酒的时候要猜拳,开头两句是唱出来的:
推开窗(窗儿)门哪,旭日往上升哪……
拳五叔,高——升!
拳五叔,七——巧!
……
时间精准,早餐来了,稀饭,馒头,鸡蛋,咸菜。我只能吃点稀饭,还吃点鸡蛋清。
一开始全是由我妻子喂的吃,等到我能坐的时候,就自己能吃了。
吃过早餐,护士交接班,交班护士领着接班护士进来,翻开我的背,屁股,说,“看,好的,全部没有问题。”就是说,我交给你的是一个好好的人,要好生照料,别给弄出什么褥疮来了。
交接完毕,上夜班的护士得赶紧回到住的地方去睡觉,准备下一个接班。接班护士则开始了忙碌。挨个发药,吊瓶,打针。
然后就听到走廊里呼叫器响起,几床几床,呼叫!
早上八点,医生来查房。医生为什么要查房?这个问题我原来一直不懂,住院多了,我基本上弄白了。就是医生根据你的病情开了处方,下了药,护士按照处方操作了。最后效果怎么样,病人有什么反应,应该做什么调整,做什么坚持。所以,查房就是我们常说的检查落实情况,就是调研。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医疗过程,医生通过查房,得到反馈,病人通过查房得到沟通,查房是双向的交流。
医生走后,病房里安静下来。这时,早上被护士打断了的瞌睡,又继续了。这样可以睡到午餐时间。午餐铃声响起,外面有人轻轻呼唤,或是一只鸡汤,或是十只鸡汤。
下午是探视时间,医院在这方面有严格的规定,一到下午三点钟,整个外科大楼走廊里挤满了人,八台电梯同时运行,上上下下,人来人往,好不热闹。不过,我的病房不让探视,我是重症病人。
到了晚上,针打完了,药也吃过了,我妻子又要将早上的工作重复一遍,端六次水,打三次香皂,搓17次毛巾。要等她把那花五块钱租的一把躺椅,往我的旁边那么一支,听到椅子的嘎吱声一响,她的这一天就算结束了,而我,则进入漫漫疼痛之不眠长夜。
病床是电动的,可以自行调节不同部位的高度。一天的很多时间里,我就拿个调控器,按那玩意儿,每一个姿势持续不了五分钟。只想,如果能坐起来,看看端正的世界,那该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啊。
要坐起来可没那么容易,伤口没合拢,是不能使劲的。据小孟说,有一个病友,已经拆线了,一个喷嚏又打开了。这种情况也许极端,但是很吓人的。我胆子小,也不敢做任何使劲的尝试。
一开始是小孟为我换药,好像是每天都要换一次。眼看着伤口一天一天长好。一个星期下来,自己悄悄的摸,脂肪比较薄的地方,能摸了,没事了,脂肪厚的地方不能摸,疼。我告诉妻子,“伤口长好了。”她要我不要摸,说手脏。
转载请注明:http://www.fifundesign.com/etzey/3358.html
- 没有推荐文章
- 没有热点文章